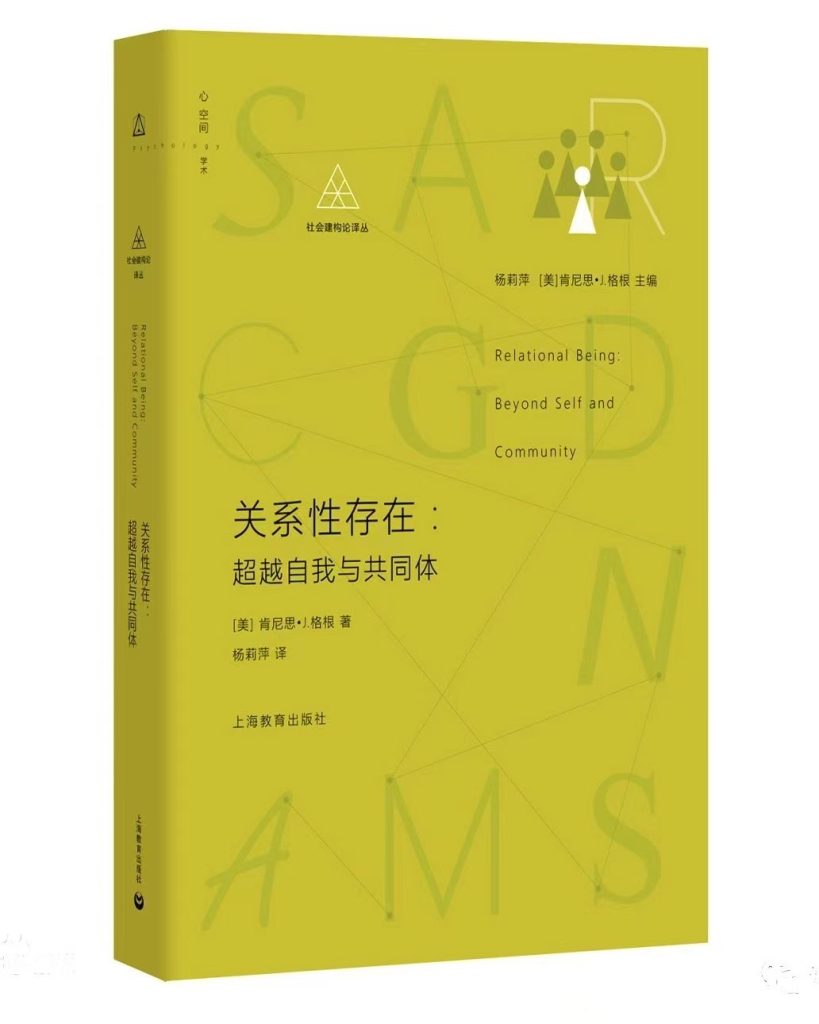
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视人为单独分离的个体、置思考和感觉的能力于个体生命的核心、珍视自主行动的观念产生于近代。这种有关人性的观念始成于4个世纪之前,我们称之为启蒙运动的时代。正是在那个时期,灵魂(soul)或精神(spirit)作为人的核心,在最大程度上被个体理性取代。个体理性坚持,每个人都拥有理性的力量,我们有权挑战任何权威(宗教或者其他力量)来宣告何为真实、合理或是何者有益于全体。启蒙运动的观点自此开始被用来为现代民主制度、公共教育和司法程序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我们渐渐接受了将个体理性作为人的自然状态这一观念。
大多数人类学家赞成这一结论。正如人类学的前辈之一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经写道:西方观念将人视为有界的、独一无二的、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动机与认知的有机体,是集觉察、情感、判断和行动于一独特整体的动力中心,与他人不同,与社会和自然背景相对。这种有关人的观念,不论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的天经地义,但置于世界文化的语境中,未尝不是一种极其怪诞的观念。
事实上,这种对于有界存在的社会通识及其在个人主义生活方式中的实现,是我们集体建构的结果。如果这种建构对我们造成限制、压迫和破坏,我们可以创造新的替代品。
眼前这本书寻求对启蒙运动传统的超越。我在努力创造一种对人类行为的新描述,以关系的视点取代有界自我的假设。这不是指相互独立的自我之间的那种关系,而是先在于人的自我概念的一种协调过程。我希望说明,事实上,所有可理解的行动都是在持续不断的关系过程中产生、维持和/或消亡的。从这一立场出发,没有孤立的自我或完全私有的经验。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构成(co-constitution)的世界。我们已然由关系中产生,不可能摆脱关系。即便在最私有的时刻,我们也并非独自一人。进而言之,正如我将要说明的,地球未来的福祉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滋养和保护关系的生成过程,而不是滋养和保护个体甚至群体。



请登录后查看回复内容